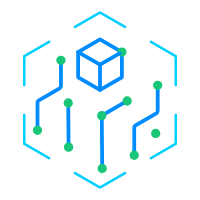章闻哲:诗歌游记 江南美学
章闻哲:诗歌游记 江南美学
章闻哲:诗歌游记 江南美学,景观视线,河流景观,景观空间分析,
在浙江诗人群中,江南诗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并非所有的浙江诗人都在写江南诗,也并非不写江南诗的浙江诗人的诗行中就没有江南韵味。在聚焦到“江南学”这个术语时,既要避免它对诗人的专制性,也要避免江南诗人对它的垄断性。通俗地说,在江南这个地域范围内,江南派,不能只指生长于江南的诗人,也不能只意味着写江南诗的诗人。但在这个民主的提示里,“江南”属性无疑会变得模糊起来,不利于我们指认只属于江南的这种美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在观察一位诗人的诗作时,什么时候,江南——作为一种风景或信息,呈现到我们面前时,根本不用大费周折地寻访,或拿着放大镜去寻找,我们会一眼认出那就是——江南。东方浩的诗就给我们这种印象。
在此之前,诗坛的一些诗人,或诗评人,已然为我们指出几位作品呈显著江南景观的江南派,他们是潘维、李浔等。较之潘、李等,东方浩并不把自己称为江南派,也不执著于江南景观抒情,然而,在量化的江南景观抒情诗汇聚成集——《从西陵渡到天台山》时,我们会欣然同意将东方浩也归入江南派。这种殊荣也许对东方浩来说,并不志在必得,对读者来说,却无疑是一种收获。对江南派来说,应该是一种扬声器式的呈现。因为,江南诗虽然因为其独特的江南水乡风光与历史人文,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柔美、婉约而风流的美学特征,不无受到一部分诗人与诗歌爱好者的追捧,但是突出的江南诗人也就这么寥寥几位。就此而论,东方浩的出现,无论如何是一种“江南的复兴”。
《从西陵渡到天台山》隐含“浙东唐诗之路”的轨迹,如果说,前期崛兴的江南派(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他们的诗歌中,或呈现出一种“江南女孩”甜美的风韵,或呈现为江南氤氲着水汽的历史人文,有一种古色古香的韵致;那么,在东方浩的诗中,更呈现出“浙东唐诗之路”本身的版图,与地域相对应的江南风光。它的历史遗迹将更为显著,它的水乡轮廓将更为具体,而它对江南不是通过词藻本身的风度来更新已然对江南人来说熟视无睹的江南,而是通过江南本身的风物与地理,更从容、更散文地展现江南。这种江南,无疑是较之纯词藻变革中的江南更古典、更本体的。诗评家涂国文云,《从西陵渡到天台山》“是一部用诗行摄录的江南影像片”——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水光潋滟,看到钓台、拱桥、台门、作坊、越剧、书院、驿站、寺院等散发着专属于江南的芬芳,那些古幽而不失明媚的书香之气,那些春燕、鹭鸟、游鱼、野鸭所带的另一种生气勃勃的水上风光,它们点缀于江南山水之间、荷花与水草之间,以及千顷之湖海之上、小桥流水之中,如同不能抵御的幽灵的诱惑,重现出江南这种兼杂柔媚与书卷气的风度。
中年诗人的沉淀与积累,使得文字本身也展示出更从容与更胸有成竹的气度。这种气度,乃使东方浩的江南诗行中,更接近唐诗意境,虽在现代旅途中而却浑然不觉有尘土车马喧嚣,只有一卷卷江南的水墨与版画,徐徐展开,令时空如洗,景观重回古代坐标——不经现代洗劫的古韵,较之沧桑更像它初生时的明丽。但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诗歌游记”,在它们集体被编入一个集子,并指出其明确的数量之时,才产生了它们对地域、对江南与地理本身的郑重其事,产生了它们对历史的某种承诺与不可或缺的对话属性。换言之,不再是一般的抒情,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雕刻于“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历史本身。这个隶属于主观,有些莫名而来的感受,并不打算在它自身的主观中承认它的偏颇,而恰恰在诗集的后记中,在诗人的自述里,从唐诗文化的数据显示里,印证了一种诗集作为一个个体文化工程与浙东诗路文化带建设之间,与当代中国丝路文化、经济建设之间的“有为”对话意图与对话构建方式里的文化地质学象征。简言之,这种景观抒情方式里,由于包含了一种地方文化担当,时代文化担当,以及经济学上的实用主义文化举措,因此变得不仅是诗意本身,而且是文化时空的严肃建筑本身。
最后一种,尤其为江南美学的一种悠久的历史,换言之,江南美学(包括诗学与江南学),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文化起兴中对于地域发展的实用主义,它产生了一种更加健朗、明丽的江南学与江南措辞,区别于普遍伤感(伤古叹今)的景观抒情。(作者:文艺评论家 章闻哲)
在浙江诗人群中,江南诗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并非所有的浙江诗人都在写江南诗,也并非不写江南诗的浙江诗人的诗行中就没有江南韵味。在聚焦到“江南学”这个术语时,既要避免它对诗人的专制性,也要避免江南诗人对它的垄断性。通俗地说,在江南这个地域范围内,江南派,不能只指生长于江南的诗人,也不能只意味着写江南诗的诗人。但在这个民主的提示里,“江南”属性无疑会变得模糊起来,不利于我们指认只属于江南的这种美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在观察一位诗人的诗作时,什么时候,江南——作为一种风景或信息,呈现到我们面前时,根本不用大费周折地寻访,或拿着放大镜去寻找,我们会一眼认出那就是——江南。东方浩的诗就给我们这种印象。在此之前,诗坛的一些诗人,或诗评人,已然为我们指出几位作品呈显著江南景观的江南派,他们是潘维、李浔等。较之潘、李等,东方浩并不把自己称为江南派,也不执著于江南景观抒情,然而,在量化的江南景观抒情诗汇聚成集——《从西陵渡到天台山》时,我们会欣然同意将东方浩也归入江南派。这种殊荣也许对东方浩来说,并不志在必得,对读者来说,却无疑是一种收获。对江南派来说,应该是一种扬声器式的呈现。因为,江南诗虽然因为其独特的江南水乡风光与历史人文,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柔美、婉约而风流的美学特征,不无受到一部分诗人与诗歌爱好者的追捧,但是突出的江南诗人也就这么寥寥几位。就此而论,东方浩的出现,无论如何是一种“江南的复兴”。
《从西陵渡到天台山》隐含“浙东唐诗之路”的轨迹,如果说,前期崛兴的江南派(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他们的诗歌中,或呈现出一种“江南女孩”甜美的风韵,或呈现为江南氤氲着水汽的历史人文,有一种古色古香的韵致;那么,在东方浩的诗中,更呈现出“浙东唐诗之路”本身的版图,与地域相对应的江南风光。它的历史遗迹将更为显著,它的水乡轮廓将更为具体,而它对江南不是通过词藻本身的风度来更新已然对江南人来说熟视无睹的江南,而是通过江南本身的风物与地理,更从容、更散文地展现江南。这种江南,无疑是较之纯词藻变革中的江南更古典、更本体的。诗评家涂国文云,《从西陵渡到天台山》“是一部用诗行摄录的江南影像片”——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水光潋滟,看到钓台、拱桥、台门、作坊、越剧、书院、驿站、寺院等散发着专属于江南的芬芳,那些古幽而不失明媚的书香之气,那些春燕、鹭鸟、游鱼、野鸭所带的另一种生气勃勃的水上风光,它们点缀于江南山水之间、荷花与水草之间,以及千顷之湖海之上、小桥流水之中,如同不能抵御的幽灵的诱惑,重现出江南这种兼杂柔媚与书卷气的风度。
中年诗人的沉淀与积累,使得文字本身也展示出更从容与更胸有成竹的气度。这种气度,乃使东方浩的江南诗行中,更接近唐诗意境,虽在现代旅途中而却浑然不觉有尘土车马喧嚣,只有一卷卷江南的水墨与版画,徐徐展开,令时空如洗,景观重回古代坐标——不经现代洗劫的古韵,较之沧桑更像它初生时的明丽。但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诗歌游记”,在它们集体被编入一个集子,并指出其明确的数量之时,才产生了它们对地域、对江南与地理本身的郑重其事,产生了它们对历史的某种承诺与不可或缺的对话属性。换言之,不再是一般的抒情,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雕刻于“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历史本身。这个隶属于主观,有些莫名而来的感受,并不打算在它自身的主观中承认它的偏颇,而恰恰在诗集的后记中,在诗人的自述里,从唐诗文化的数据显示里,印证了一种诗集作为一个个体文化工程与浙东诗路文化带建设之间,与当代中国丝路文化、经济建设之间的“有为”对话意图与对话构建方式里的文化地质学象征。简言之,这种景观抒情方式里,由于包含了一种地方文化担当,时代文化担当,以及经济学上的实用主义文化举措,因此变得不仅是诗意本身,而且是文化时空的严肃建筑本身。
最后一种,尤其为江南美学的一种悠久的历史,换言之,江南美学(包括诗学与江南学),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文化起兴中对于地域发展的实用主义,它产生了一种更加健朗、明丽的江南学与江南措辞,区别于普遍伤感(伤古叹今)的景观抒情。(作者:文艺评论家 章闻哲)
相关文章
- 这么做设计思路清晰竞品对标五大景观亮点三级价值投入
- 英式风格长沙橘子洲又添一处百年历史景观免费开放!
- 益阳文旅产业火了:休闲旅游时代游客纷至沓来
- 罗山县定远乡:“小景观” 扮靓乡村人居“大环境”
- 南方日报:大数据风光无限的另一面
- 北京16区晒部门预算 三公支出持续下降
- 35座瞧一“桥”有多好看
- 石家庄珠宝首饰手绘培训专业效果好
- 广东产地分享黄蜡石招牌刻字石村口题名景观石这样黄颜色的石头你喜欢吗
- 山西一旅游风景区有八百里最著名的自然景观有避暑天堂之称
- 细数香港十大文化景观
- 只为超越传奇而生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别墅产品迭代
- 梁平膜结构景观棚包工包料包安装
- 闽江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美化榕城语言景观服务地方文化建设
- 浙江日报 数字报纸苏州新景观
- 成都周边这些被风景包围的民宿藏着一个个诗意栖居地即将美出新高度!丨南方民宿
- 有幸买到独栋也要将水泥顶砸掉换成木格栅在室内打造天井花园
- 晒晒农村的房子鱼池、菜园、景观一个不缺城里人也羡慕!
- 相关文章独墅湖景观
- 天然英石青龙石室内鱼缸景观打造观赏风景石